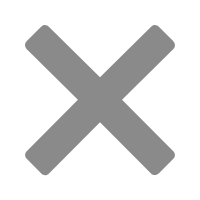2
意识开始变得模糊,疼痛和饥饿交织在一起,让我产生了幻觉。
我好像看到了妈妈,但不是那个跪在田里学狗叫的妈妈。
而是一个手里拿着剑,站在高处的妈妈。
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候,那些以前被我忽略的细节在脑子里转了起来。
小时候我不懂事,跟着村里的小孩一起笑话我妈。
王大富让她跪在麦田正中央,让她学狗叫驱鸟。
“汪!汪!”
那时候我只觉得丢人。
别的孩子都有妈妈抱,只有我妈是个“稻草人”。
可现在想想,哪有正常人能像她那样跪?
她一跪就是一天,从太阳出来到落山,纹丝不动。
哪怕是大夏天太阳晒脱了皮,冬天的雪盖满了头,她的脊背永远挺得笔直。
那根本不是跪,那是站桩。
即便身上穿着最破烂的衣服,脸上涂满泥巴,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精气神,是掩盖不住的。
我给妈妈送水时,看到她的手上有一层老茧,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干农活磨的。
但我错了。
干农活的老茧是在掌心和指根。
可妈妈的老茧,在虎口,在食指的侧面。
那是常年握兵器留下的痕迹。
还有那次,我看着妈妈跪在田里,觉得好玩,也学着她的样子想去“站桩”。
一向温吞吞、呆滞的妈妈,突然冲过来将我推开。
“别学我!二丫,别学我!”
她那天吼得嗓子都破了,眼睛红得吓人。
“你要读书!你要走出去!永远别学这没出息的样!”
那时候我被吓哭了,只记得她随后就被赶来的王大富用鞭子抽了一顿。
那鞭子抽在她身上,我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,可她一声没吭,只是死死护着我不让我看。
后来我才知道,她腿上那几个圆形的伤疤,是钢钉留下的痕迹。
听村里的老人说,当年王大富把我妈买回来的时候,她打倒了三个壮汉才被按住。
最后是王大富让人把她的腿骨敲断,打了钢钉才让她老实下来的。
原来,她不是天生就是跪着的。
她是被人打断了腿,不得不跪。
棚屋里太冷了,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我又想起那一晚,我饿得睡不着。
妈妈就会教我一种奇怪的呼吸法。
“吸气……停住……慢慢吐气…….”
她说这样就不饿了。
我照着做,身体里好像有一股暖流在动,饥饿感真的减轻了。
那时候我以为这是穷人的法子,现在想来,那分明是吐纳法。
还有王大富家门口!
他家门口挂着一把生锈的剑,说是“辟邪宝剑”。
每次经过那里,妈妈眼神就会变。
以前我以为她是怕那把剑上的煞气。
现在我知道了,那是看到自己丢失的武器时,想要拿回的渴望。
这些零碎的记忆,在慢慢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真相。
我妈不是傻子,不是疯婆子,更不是天生的奴隶。
她是鹰,被剪断了翅膀,困在了这片烂泥塘里。
我费力地翻了个身,断了的肋骨戳得我一阵冷汗。
但我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烧。
因为我手里握着一个秘密。